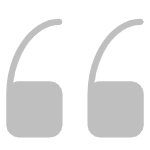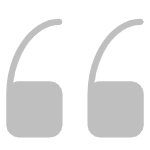我自己曾坐在佛羅倫薩的亞諾河畔�����,思考著一個文明��,一個文化���,寫下了《叫做亞諾的河流》,我思考著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���,這里的人經過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�,承受宗教對于人的壓力���,一種禁欲,對欲望的不可討論�����,才慢慢地����,一點一點地從宗教的禁忌中掙脫,去確立人的意義����,開始畫人��。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的蒙娜麗莎坐在那里微笑���,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肖像畫而已,它標志著一個人可以被當成人看待的意義與價值��。
我自己曾坐在佛羅倫薩的亞諾河畔�,思考著一個文明,一個文化�����,寫下了《叫做亞諾的河流》���,我思考著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��,這里的人經過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�,承受宗教對于人的壓力�,一種禁欲,對欲望的不可討論��,才慢慢地�,一點一點地從宗教的禁忌中掙脫��,去確立人的意義�����,開始畫人�����。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的蒙娜麗莎坐在那里微笑����,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肖像畫而已��,它標志著一個人可以被當成人看待的意義與價值���。